汉心:艺术仍有应境而发的神意参验
| 作者:[汉心] |
|
|
|
时下中国,流弊所致,文艺生态主题扭结、旨趣错位,在眼花缭乱的戏码章法中各显神通,不是弄潮造势,便是以奇淫巧技先声夺人。所以,就算是阅了荣华、出了风头,但却仍少有印象深刻直抵人心的活性书写和流芳品质。数十年先锋主义兴风作浪,文艺躲避崇高,诗性隐遁造成的精神污染与道德空场,不仅风干了中国文化持久的人情参验和悲悯泪点,还因一班好事者不断穿越解构,戏说而衍生成一派寻欢作乐的“小时代”精神,在拉低中国文艺品位的同时,其价值虚无引发的认知混乱,不单是毁了三观,降了人格,伤了和气,还因谬种流传、小品压轴推波逐澜,将社会习俗导向轻佻油滑、无明妄行。由此造成的文艺旨趣,既少了蓬勃的青春叙事和励志美学,也很难合成端肃大方,躬行文教的风雅正气。 由此,文艺学上表征的便是,也只能是标准失序和中心崩析,一切都是基于市场分利起哄炒作而各表章法,由此形成互不认账,彼此拆台而只顾自圆其说的江湖乱。即使出于文宣规范而需要态度端正、作风高尚,也因缺少严肃的意义诘问和信心指向,只能任由操弄者自命正确然后恣意挥发,其无所用心催化的创作盲动,既不能诉诸意气风发的美学舒展,也无助于修身正性化民成俗。所以,西奈山上有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说,文化一乱搞,世间便没有了是非。至此,艺术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户,既无需深入民间知寒问暖、师法造化采天地之灵,也不必感时忧世,长太叹息兮以掩涕。所谓资本搭台、文化唱戏便只能是反复拔弄投机取巧、争锋套利的消谴趣味和群氓联欢,看起来热闹,但无不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乡愿扯谈,正所谓“风乍起、或可吹皱一池春水,落幕处,一切归零”。所以,有学者说,娱乐文艺或许可以兴趣十足,也可以激发市场围观,但却仅仅流于话语挑拔或基于好玩的诛心之论,它很难触及到人的生活,也改变不了人的感觉和对世界的体认,这时候,人们关注文化不是基于信念和热爱而是消费,是心不在焉的时尚扮相和个性化的逗趣摆拍。 这足以印证一个古老而朴素的因果逻辑,即有术无道则行之不远。空壳化的创意推广或许可以标新立异,也不乏喧嚣而且敛得人气扎堆、买家捧场,但其一路取悦媚俗,折射的不仅是大时代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是当下人文馈乏和山头主义泛滥导致的美学贫血。殊知,体制疏漏、市场无序或许可以容忍个人离经叛道搞艺术造反,但精神亏欠野生的浮夸一旦成为流行主调,则魂不守舍的文化因缘际会,即使花哨风流,但总会因缺少耐心沉淀而势必将所谓创意冲动引向临场发挥,即时行乐,或仅仅基于价格套现便可以见利忘义甚至讨好受众。自此,立足当下的效用考量,必然省去苦心孤诣的严谨态度和深耕细作,在急火功心,名利通吃的双重鼓动之下,艺术不仅无助于勃兴乡土文化自证光荣的期待与梦想,也很难展现其应然的美学质感和精神气魄。 一般而言,文艺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写意抒怀,陶冶心性,也是见诸芸芸众生和谐自洽、辉映成趣的生活方式,殊知,中国传统美学正是缘起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情感和精神修正, 它植根于人的本真心向, 是从对现实处境的肯定与人生体贴出发,把世间问题置诸一切灵感的源头, 从而在现实与彼岸之间寻找接口。所以说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其意义不单是促人向善、安抚身心,还是亲疏相顾、其乐融融的情感符号和精神家园。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诗情画意不仅有自足的内生机制和经受时间与历史筛选的韧性,还承载了不可替代的气质风度和交流语码,它取决于中国社会千年累积的经验和可通约的价值体认,并由此而内化成为识别中国身份的美学趣味和观念形态。 是故,凡中国人皆必然对应于其中,诉诸诗书文教修身正性,齐家治国,不仅是中国人的日常功课,也是体察世风民情,论断是非得失的学理基础。大而言之,可以涵盖社会观念和民族精神,甚至左右国家意识形态,小则事关饮食男女,郁结于伦常情事并定义着人们的心理偏好和行为方式。缘乎此,一种文明装置及其旨趣之所以能照应人心、发扬光大,在相当长的时期有效而且构成了义涵丰富的历史叙述。就文化发生学而言, 不单是族群优越的知识系统, 也是共同体团结奋进的心智集成。至此,其超越性的意义就不仅止于确认历史如何正当,过去如何美好,还能据此建构统领未来社会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其预设的愿景与梦想, 虽不能全息表达多元时代的人文性情和价值诉求,但至少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对中国精神重显荣耀的前景保持乐观,从而懂得薪火承传的关切与护持。 基于此,我们仍然要基于信心和文化想象,甚至虚构某种情景对可能性作出至善至美的预设,尽管仍有无法逆转的冷嘲浊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会放弃拔邪树正的担当为生活做美好的价值导航。或许,就其功能无关大局,也不经世致用直指当下救济民生。但从个人经验和师友间流溢的心怀之中,我们仍能触及到一种宏思远益的精神质感, 这当中有如书法家杨明,其秉赋始终饱含了某种为艺殉道的狂热与冲动,故他总能以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的耐力,陶然于自我的造境写意而不动如山,或许,他仅是个人化的心领神会而无涉明确的文化主张,也不倾向于某种别开生面的美学归类,但其数十年意气风发的率性书写,却颇有千夫诺诺不如其一士谔谔的洒脱与倔强。从其砥砺精进的书风来看,杨明也有些许师法古意,远避现代潮头的遗老心气,故其作品总有一种不染浮华的孤芳自赏,虽置身市井烟云,有不了红尘酬酢周旋,但却总能在落笔处捣碎纤巧附丽的技术妆点,绕开曲学阿世的流风与造作。正是基于此,其墨相除却一向疏阔突兀、耿介厚朴之外,近期作品的立意布势和构形更是多了些歪打正着,不见精心运筹的通脱与任性,其开合大度、真气外泄的挥发不仅彰显了他驾轻就熟,万象皆备于我的游逸风范,更是透着物我两忘、明心见性的古道热肠。 从生活价值上讲,人无非三种取向,或重复昨天的故事随波迁流,或追名逐利建功立业,而最具自性品相的活法则是流落江湖,不治生计的诗意栖居,杨明或许也憧憬着这种淋漓酣畅的快意人生,故总有一种慷慨赴义、逆势而行的执拗,其缘起性空而不被流风侵扰的“独门心法”与别样体验, 除了不落窠臼,一住情深,也是其睥睨当下艺术屈尊降格的反戈一击。总之,如此书写心境之章法路数,不仅成全了他别开生面的豁朗气派, 也突显其不染俗念的活性品质,于那得心应手的木棒之舞画写乡愁古意,就算是不能在水一方开宗立派,也可以于此重温沾风带露的处子情怀吧!所以,他始终犹如站在悬崖边上遗世独立的“剑客”,由于内在的自由使其生命充满了意义,故他总是倾向于一种任性的精神浪游,将心中的书写意象置于怪诞的现实之外,然后秉持着真性情寻找艺术的落脚点。
杨明知道,盲目的生活会消蚀掉生命本应有的神彩,因此他力图以一种内窥然后仰望的豪迈寻求精神的突围。所以, 总是能弹指挥去市场名利烟熏火燎而后独享诗性的况味。是的,艺术总有不能忍受的媚俗之轻;也有无法抗拒的时代调性, 佛说凡人皆著人我、众生相,谁都不可了脱俗业知见,达于觉者澄澈不染之境, 而杨明正是体恤缘起因果造作的种种乱象,所以才会数十年经略木棒造形、独树一帜, 而后超然物外晓以另类的书道化解当下的急功近利!人都希望活出烂漫,活出有意味的纯度与光华,即便仍有重重牵累,但只要是有仰望、有心怀,有陈义高妙的灵性表达和应境而发的神意参验。就能通过鲜活的作品见证其不同凡响。一般地说来,擅艺者都耽于不切实际的妄念,都有精神向度的冲撞和不能靠岸的错愕与惊惶,也只有这样, 杨明们才能将有限时间中那些有脱俗的意象与某种绝对真理关联起来,从而便可以在世态迁流中葆有活性的书写和流芳品质。 |
(责任编辑:清风)


 江南入砚——姚新峰
江南入砚——姚新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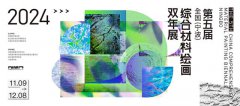 2024第五届全国(宁波
2024第五届全国(宁波 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
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 专家称全网关注的观
专家称全网关注的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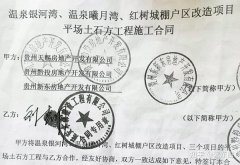 贵阳乌当:棚改项目
贵阳乌当:棚改项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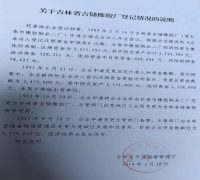 吉林省市场监管王淑
吉林省市场监管王淑 官商学联合起来
官商学联合起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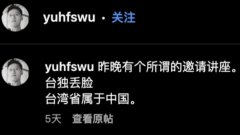 瑞士砍杀幼儿的
瑞士砍杀幼儿的 湖南人权捍卫者
湖南人权捍卫者 400人强拆河南大
400人强拆河南大 卷宗证据实锤:
卷宗证据实锤: “宛如地狱”
“宛如地狱”